2023年12月21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校庆百场学术报告暨“政治过程与中国自主知识生产”系列报告会在法商南楼135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实证方法论到实践方法论——历史社会科学的谱系”。报告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罗祎楠主讲,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向民主持。政治学系系主任王逸帅和臧术美、师义帆等诸位老师参与了讲座。

讲座伊始,罗老师先抛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认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他指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其讨论实践方法论的根本问题意识。过去一系列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似乎已经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规范的方法操作流程,但这就是全部吗?
李丹(Daniel Little)有一本书《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该书通过梳理和比较西方对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研究中的众多理论背后的方法逻辑,认为现有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规范性(normal)方法,即研究者按照一定方式操作就可以保证研究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另一类是描述性(descriptive)方法,即研究者应将自己真实的研究过程本身视为方法,研究本身也作为一种被解释的过程。

罗老师指出,尽管李丹对于第二种方法的讨论并不充分,但是这种描述性方法论自觉在英语世界内并不少见。Howard S. Becker的《社会学家的窍门:当你做研究时你应该想些什么?》(“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和“Evidence”两本书中都表达了希望作为一个研究者和读者展开对话,作者的研究过程不仅包含了作者对于读者状态的想象,也包含了作品被理解的过程。另一本相关的书是Ragin, Charles C.、Becker, Howard S.和Ragin, Charles C. 合作的“What Is a Case?: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案例不只作为一个客观研究对象被加以审视,而是在研究者不断变化和调整的认识和理解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因而只有对思维的基本单元重新进行现象学还原,重新将其纳入对认识过程中加以分析,我们才能够去理解和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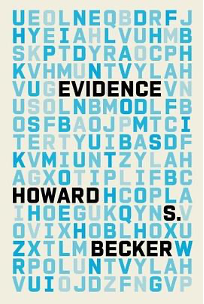
在这个意义上,“方法”开始被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但这样的思想源流尽管跟现象学有密切的关系,但并非源于现象学的发展。真正将这种方法论思维推进的哲学动力是来自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研究(Pragmatism)。我们过去通常将这种实用主义哲学视为一种社会改造理念,但实用主义哲学实质上是一种认识论问题,是以回到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本身作为构造整个社会科学的拉动力。罗老师认为,美国的社会科学对于全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就在于,美国成功地将实用主义思想贯彻到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之中。C.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提出的“imagination”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识论的基本概念。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的研究更为典型,他认为人需要在不断的理解自身的过程中去展开对于世界的认识。简单来说,不同于笛卡尔的“我思”(cogioto),研究者要将社会研究视为一种社会行动,是一种实践活动。处于社会之中的人,趋向于将行动与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图景联系在一起,并从中找到自身在整个社会世界中的位置。在此过程中,人从自身的原始感受出发,不断的理解自身行动的意义。中国相似的表述则表现为“实事求是”,即研究人们如何在“实事”中“求是”。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始于一种本真的surprise感受,当过去认知世界的模式无法解释现有的变化时,反身性思考(reflection)成为可能。当我们重新思考如何理解原先哪些“观念”所不能理解的新的体验时,我们才开始把这个世界中原先没有被“手电”照亮的体验重新照亮,知识的边界才得以拓展,一个新的世界图像开始出现。
美国实用主义研究就是探讨真理是如何在人们不断改善的认识中生成的,这种思维模式对全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原先是由舒茨带到美国,和美国的实用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对研究过程的认识论讨论。例如,芝加哥学派的扎根理论要实现的是一种认识过程的自觉和理性化,要超越实证研究中的编码思维和变量思维走向“理论化”(theorizing)。“理论化”意味着理论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反身思考的过程,认识世界的过程永不停息,因而理论永远在进行之中。Richard Swedberg有一本书叫做“Theorizing in Social Science: The Context of Discovery”,其中“From Theory to Theorizing”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对研究过程的认识论讨论在英语学术界已经发展了上百年,但是在中文学术界却还没有完全展开,且不同学科的进展不同。就哲学而言,部分学者已然指出,哲学的本质问题是实践问题,哲学史研究若脱离了实践意义上的哲学(practice of philosophy)将走向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就史学而言,历史阐释流派认为实证史学的研究路径会带来碎片化的研究,而后现代则否认了事实证明的本身,走向了笛卡尔的我思的怀疑论。历史阐释的本质就是要把人们认识历史的活动本身视为“真实”,即把对世界的认识过程带入对世界的理解中去。社会学领域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不多,其中具有开创性价值的是费孝通老先生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文章指出,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首先应回到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中,“经世”本身是一种对时代的理解,即回到“人如何理解他所处的世界”去理解时代。
费老晚年提出我们需要去借鉴国外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通过社会理论的反哺帮助我们重新打开中国传统以“经世济民”为中心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此后,2012年底的由期刊杂志和高校合办的“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学术研讨会实质上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关注历史过程的方法论转向。在此学术脉络下,周飞舟主张回到传统对社会的理解中去观照当今时代;应星强调回到革命共产主义时代;渠敬东则强调文明互鉴视角下经验、理论与历史的融通。正如卢梭从原始部落开始谈起、马林诺夫斯基从土著人和原始社会谈起,我们这个时代文明所遗忘的东西可能在其他文明中还存在着。先秦的老子庄子与19世纪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不期而遇,优秀的思想家总会在某个时刻达成某种一致性。文明之间的时空错差有助于我们重新把握那些被遗忘了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
而政治学对与实践问题的讨论格外重要。现有的现象学政治学虽然不是从方法角度来讨论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回到认识过程本身”的方法奠定了哲学的合法性。田野政治学的发展强调从事实出发,对田野政治学的方法论层面的推进实际上是历史质性思维的体现。而历史政治学背后同样蕴含着实践社会科学的意味,学术本身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实践,因而扩大史观成为必要。
再往前追溯,回到认识实践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的基本看法,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段开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都旨在超越纯经验的实证研究和纯理念性的研究,将研究活动本身对象化,这实际上是实践哲学最基本的特点。
基于以上对不同流派的梳理,罗老师详细陈述了其关于实践方法论思考的学术脉络和背景。无论是经验哲学、历史阐释学、历史转向,还是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这些流派都共享着对于实践主体性的认识,即要回到人的实践中去获得对于自身实践的理解。换言之,任何的“法”都是人、事中的一部分,“法”即方法。因而,在中文语境内,实践哲学的推进也更具重要意义。
罗老师认为,中国学术界从49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纠结于古今中外的问题,但却丢失了关于我们作为人之本真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人的世界的奇妙之处在于,人可以将完全不想干的知识系统整合进自身的精神和实践中去,这种整合因而具备了超越古今中外的力量。“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所以只有回到我们自身,从而理解古今中外,最终汇聚到理解我们时代的过程之中。“反求诸己”,找回我们自己才能找到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的方式,才能找到我们在这个时代中自处的方式,而这种思维也正是我们重新理解中国学术方向的重要方法。
当我们谈到实践方法论或是历史社会科学体系的建立,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靠近我们理想中的研究?即支撑我们研究的背后的那套理解是什么?Hilary Putnam在他的“The Collapse of the Fact/Value Dichotomy and Other Essays”一书中指出,没有norm,我们将无法获得facts。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找到一个全面的客观的理解世界的方法,否则我们将抛弃我们回到认识过程本身这一哲学基础。按照尼采谱系学的路径,谱系本身是主体眼中观照出来的世界。任何的认识过程背后都有一个规范性(normative)的标准,但问题在于研究者是否能够自觉意识到背后norm的存在,并向后人敞开,为后人所讨论批评。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方能观照到其他的研究方法及其特点,进而明确自己研究的理想状态,这也是罗老师称为“外部视角”的第一个最基本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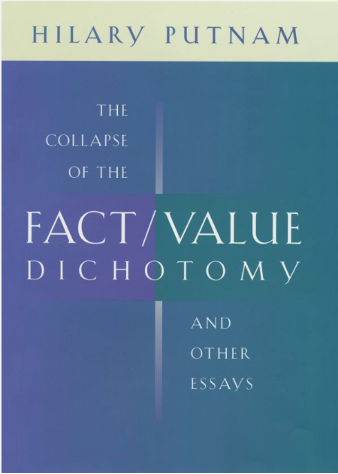
第二个特点则来自“内部视角”,即任何的研究所声称的研究方法都无法概括其实际展开的全部过程,而我们还应该看到研究者“言说之外”的行动过程。实证研究强调识别这个世界的客观属性,但从内部视角出发,那些客观属性也是被构造出来的,因而研究者不应该从上帝视角去发现客观属性,而是要将构造过程本身纳入公开分析。罗老师指出,以上两个特点构成了其认识实践的视域,在此视域内得以重新理解方法问题和方法流派,从而有助于重新构造谱系,而谱系的重构提供了分析认识过程的新起点。
无论是西方对理性选择理论前提的批判、还是布尔迪厄的反身社会学,或是阐释学的反身性研究、又或是上述中国学术界对理论视角的反思,这些讨论仍然是注重本体观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把认知全过程纳入分析讨论。而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通过消解认识论问题讨论经验研究,使其分析沦为“空转”。爱尔兰学派在讨论知识是如何被学术共同体接受的背后,也存在均质理性人的前提预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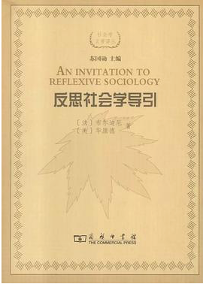

实践方法论作为一种理解研究的方式,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切身性,一个是主体间性。对于这两个维度的理解要重新回到对“认识过程的过程性本身”中的“过程性”(processual)一词的理解。这一概念源于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的《过程社会学》(processual sociology)。“过程性”本身作为一个不断绵延变化的过程,按照胡塞尔的形象比喻,就像几何学中的点和线,连贯的线由无数个点画成,因而线上的每一个点都蕴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重时间性。在现象学对时间的基本认识中,当下是一个包含着过去和将来的时间绵延。因而,“过程性”的理解世界就不能把世界分解成点状的、模块的社会结构、个体人假设等要素,回到认识过程本身的分析意义在此得以凸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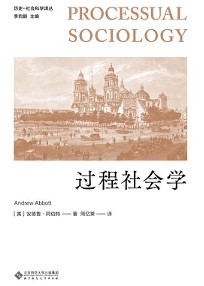
罗老师进一步说明,所谓“切身”,即切身之不契合感的产生使研究者重新反思自身学术思想的来源,从而用新的视角去构造世界的途径;所谓“共在”,即以自身视角反观其他常识,进而比较两者的差异。过程性的延展来自于人的切身感受的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世界图景被重新建立。作为行动主体的人之间的共在互动,即使无法达成完全理解,也可以在自身世界内观照对方。当我以我的主体性观照他人时,也为他人用他的主体性观照我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理解”的意义得以呈现。
“过程性”本身没有一个永远的起点,每一个“起点”都会被重置于反观之中。因此,基于实践过程的切身性和主体间性也为颠覆现有的认识提供了可能,而这个颠覆的基础则源于“实践性”。相似的观点可以用朱熹的“法”来表示,这种介于规则意识形态之间的方式只有在研究具体问题的导向下才能转化为具体可见的方法。

最后,罗祎楠老师指出,对于实践过程的方法论讨论背后隐含着一个更大的关怀,即学术共同体自身的构造方式。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不在于树立权威论证自身的正确性,或者再造反叛者将其推翻,而在于研究者基于共同的方法认知展开对话,后人将前人不断纳入反思。换言之,只有当共同体成员就具体方法和方法产生出来的研究本身展开对话时,共同体的链接才得以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