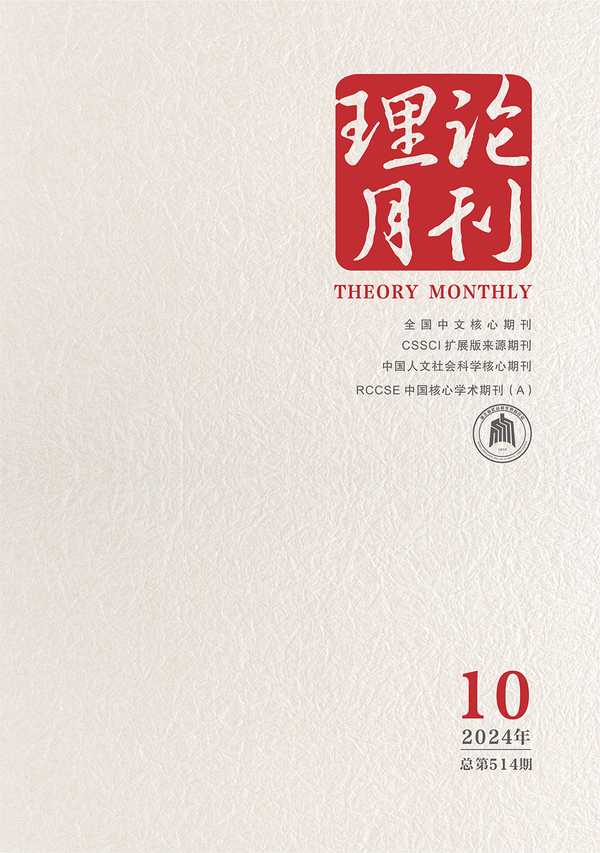近日,我院王向民教授在《理论月刊》2024年第10期“基于中国实践的政治学概念研究”笔谈栏目发表文章《回到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政治学史研究的概念建构》。公众号转载全文与读者共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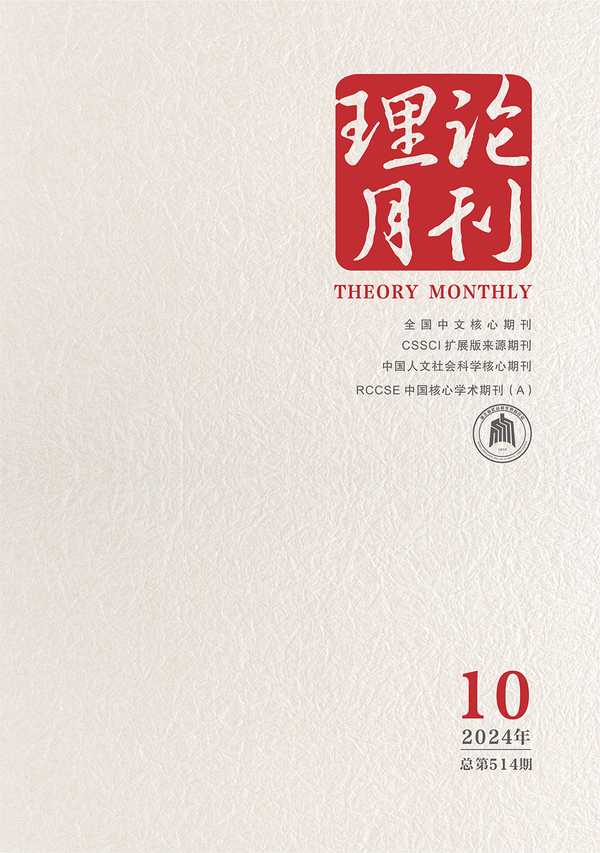
历史研究特别警惕从概念出发,用概念或理论裁剪过往事实,因此它采取叙事而非分析的写作模式。然而,在处理学科史的研究对象时,它仍然有可能落入从概念出发的窠臼。这里的概念是指后来形成的研究对象的名称或符号,历史学研究者由此研究对象名称而回溯其早期发展过程。殊不知,此符号本来就是一个概念或历史建构的产物,由此符号出发,已经无意识地陷入前面所说明的从概念出发的研究过程,使历史研究变成用概念裁剪过往事实的学术过程。因此,史学研究强调不断的“再历史化”过程。政治学史研究就是一例。现有主流的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大多接受了美国政治学的学科界定指标,即现代大学教育中的政治学系及其职业社团带来的共同体身份认知(政治学会)。由此,将政治学史理解为“政治学系”史,政治学史的故事就是各个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的历史故事。目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皆有专书,都是这种思维构造的写作方式。而对于另外一些研究者来说,现代学术写作的“大问题,小切口”原则也使其将具体的大学院系选作研究切口。然而,当回到历史本身的脉络尤其是知识建制与政治情境的同频共振时,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历史面貌。学科面貌变更的背后是主政者的替换。为京师大学堂提供第一份章程的梁启超照搬了其主持湖南时务学堂的《功课详细章程》,他对新机构的定位是政治学院,即训练与供给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新式官僚。然而,等自日本尤其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主政京师大学堂的时候,京师大学堂就转变为日本式尤其是美国式的知识生产机构了,乃至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彻底截断了京师大学堂的政治训练职能,使其成为现代知识生产机构(所谓“大学独立”),尽管北京大学仍然在现代大众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从京师大学堂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首先,从“政治学”这一现代语词来讲,现代汉语是从日本和制汉语迁移过来的,是否尚无此语词的过去便是无此事实的历史?倘以此论,“政治”一词也是和制汉语的发明,那么,19世纪末以前,中国是否便没有“政治”之事实?因此,以“政治学”课程或“政治学”系科冠名的历史都是以“概念”倒放电影的历史。其次,梁启超在书信中曾明言,以“西人政治学院”为湖南时务学堂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摹本,但尚未出洋,更不懂洋文的梁启超所谓的“西人政治学院”是否如法国人真实理解的“政治学院”,也未可知。唯一可以断定的是,梁启超的语境是培养“政才”,亦即清廷改革需要的新式政治人才,故此学院意在培养新式官僚以供朝廷所需。再者,当时的美国,尚处于传统学院(经院宗教训练)向现代大学(知识生产)转型的阶段,大学内设置系科是一种探索,并未定型成为标准。学界所据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建立于1880年,而从身份意识上表明政治学与历史学研究不同的象征则是1903年从历史学会独立而成立的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至于欧洲,迟至二战后政治学才逐渐从传统的法学、历史学建制中独立出来。在此语境下,更难确定尚未模仿美国的1895年京师大学堂的设置便有系科独立的学科理念。所以,用美国政治学的“政治学系”或现代“政治学”语词的标准去量度中国近代的政治学史,便显得生硬而不合历史语境。因此,从事物的功能(赋名原因)而回到历史事实(语境),更贴合历史研究的真谛。政治学的功能(元问题)在于为政治实践提供知识论证,“现代”政治学为现代政治提供知识论证。以此而论,此处的“政治学”实则“政治知识”,任何文字发达的政治共同体大概都会有发达的政治知识论证,故而也有其作为历史事实的“政治学”,尽管它可能并未采取“政治学”或“Politics”“Science of Politics”“Political Science”的语词称谓(当然,语词的出现,表明它在语词所表达的意指上更为明确,更有针对性)。传统中国有发达的政治合法性论证(天、道、理、气等),也有发达的官制记述,更有政治与行政的原则或实践叙述。更重要的是,在被现代西方学术分科制度打散之前,中国传统自有“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史子集”范围或外延有所变动,但是,“经”这一语词的含义与当下政治学知识论证(尤其是政治哲学)几乎重叠。当然,我们会说,政治学的指称本意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意指一种特定的政治知识论证,即对“现代政治”的论证,“现代”是它的身份证。如此,“现代”政治学作为一种“后来者”指向的语词,便带有强烈的强硬、侵略与固执的意识形态属性,合我者为政治学,不合我者不是政治学,而不是一种基于普遍性界定的概念。因此,我们看到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验并未在国际主流政治学界得到回应。然而,伊斯兰世界从古希腊开始就与西方并行,甚至一度在地域竞争中处于上风,从史学角度说,谓其没有政治学如同视他们仍然处于裸猿期一般,尽显意识形态的知识霸权意味。如果我们以现代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知识,以政治学系为判定指标,那么,我们将看到,欧洲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使政治学与历史学、法学逐渐区别开来。而美国的学科分化行为,则是一系列“寻找差异”行动的结果。在理念上,美国现代政治学家秉承国父们的遗愿,论证美利坚政体(The American System of Government)不同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威胁”的欧洲政治而有“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在社会群体划分上,充分世俗化与职业化的美国政治学家日益将自己与政治实践者及其他政治评论者区分开来,倘若说约翰·伯吉斯(John W.Burgess)、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等人尚是美国东北部的参政士绅,那么,20世纪之交执掌美国政治学会的古德诺(Frank Goodnow)、本特利(Arthur Bentley)、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等人已经是“从学校到学校,才下课桌便上讲台”的职业研究者了,只有后来成为总统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一个例外。因此,美国政治学系的学科界定毋宁说是美国社会领域的职业细分以及由此而来的职业岗位的社会空间,亦即学术分工的细化与专业化的结果,正如商业领域的细分市场一般。没有政治学系,就没有政治学家所供职的组织单位;没有政治学系,就没有政治学家的工资薪酬来源,政治学系成为政治学家的肉身生存之地。进而,政治学的学科版图日益细分乃至于几乎要消解政治学的统称称谓,如今,还有华勒斯坦所说的、近代早期形成的、与经济学社会学并列的、统属性的政治学吗?!倘若不是做学科史研究,专注于自己的小领域,笔者大概也不会持此种宏观视角。因此,回到事实,在比较视野中从元问题出发,才能更好地回到历史语境,才能更好地界定地域形态的历史特征,亦即寻求到本土性或地方特色并完成概念建构。从现代政治的知识论证角度说,美国政治学伴随美利坚政体的知识论证而生发,经历了建国政治学、建国理念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型以及以政党、选举等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作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政治学的研究者身份、知识内容、知识偏好、学科任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我们从后来者的语词出发,不愿将其归为一条内核一致的政治学史的知识社会学分析路径。《联邦党人文集》是美国论述的核心文本之一,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政治科学”(Science of Politics),“那些对于古人来说理解得不全面的或根本不知道的各种原理和功效现在已经得到了极大的理解”。因此,《联邦党人文集》与其说是一部联邦党人的政治布道,不如更准确地说,是美国建国者的政治科学,而后来作为学术分科的政治学家只是相对于早期立法者的阐释者而已。国父们的建国政治学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亚当斯(John Adams)在1776年(美国独立那一年)写给威廉·胡珀(William Hooper)的信中作出了更为清晰的表达:“政治(学)就是人类幸福的科学——而社会的幸福则完全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政府的章程。”这一历史过程,在沃尔多(Dwight Waldo)的笔下,被表述为关注公民教育与“市民文学”,建国者认为政治学的责任在于培养美利坚合众国所需的公民,因此知识教育与公民训练是政治学的核心任务,而知识教育的文本则是建国者的政治论述(例如《联邦党人文集》)和政治机构的政治文件(例如总统讲话、国会辩词、司法判决、政治家演讲)以及报纸杂志的社论。这是一套不同于现代大学体制的政治学形态,相较于“知识生产与发表”的单一形态,它与现实政治实践的关系更为紧密,知识生产与话语论证服务于政治实践而非有其独立存在意义,这更能够回应“政治知识论证”学科设置的实践论指向。因此,它也被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写入美国社会科学史之政治学部分。中国政治学史显然比美国政治学史更复杂。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和欧洲传统之间的连续而非彻底断裂的特征,美国接续了欧洲近代的政治、社会尤其是文化思想观念,或者说美国思想本来就是欧洲思想在新大陆的拓殖,并不存在一个分庭抗礼而不得不融合的传统;另一方面,美国对欧洲的接受并不存在语词(表述)上的差异,英语或法语的现代化在欧洲已经完成,美国流通的语言已经是现代语形式。然而,中国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内含着一个更为重要的危机,即语词表述危机,从古代文言文向现代汉语的转型。现代汉语的形成,并不以翻译学所主张的“信达雅”的真实对等为原则(严复的译词最为精确,真实可信,却因其文言形式而被抛弃,和制汉语因其简单易解而被大众所传播),而是因应近代大众运动(例如发达的近代报纸系统与大众街头运动)的选择性需要,是一种全新塑造,它以大量的复合词取代了传统的单字,从而将传统中国的细腻区分逐渐抹杀而形成现代观念。例如现代的“政治”一词,传统表述是“政”与“治”,是两个词及两种含义,现代词“政治”已经去除了传统“政”与“治”的某些含义。1920年代初的现代汉语定型,坐实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隔膜,从语词表述的根脉上发生了全盘性危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肇端与中国现代语词的转型相依相随,政治学新词的出现,同时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概念的转型以及政治新词的发明。倘若以政权更迭为建国立法的指征,那么,20世纪的现代中国实则有两种建国知识,一个是孙中山创造的“三民主义”,一个是毛泽东思想。对政治学尤其是中国政治概念系统而言,前者的影响从辛亥革命一直持续到1949年以及此后的中国台湾地区,而后者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供给远比政治学界的概念创造要多,甚至正是因为政治学界概念创造的匮乏导致政治学家只能作为阐释者而非独立学术者,而其学术创造的落后又影响到它在政治与社会领域的职业身份角色的独立性及其社会评价。民国时期大学体制下的政治学家,负笈欧美,师承国际前沿政治学大家,归国后开创了现代政治学在大学内的系科发展,建章立制,著书立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然而,他们更多是将西方学术引进来,关于中国的论述却较少,用来研究中国的分析性概念更少。尽管民国学人已意识到学术本土化的重要作用,1930年代有“十教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但是,时代赋予民国政治学家更多的是学术传声筒角色,落后挨打下的西学东渐、救亡压倒启蒙,使政治评论甚于学术创造。这是一个类似于美国东北部士绅和初步职业化政治学家创建现代政治学的历史过程,但是,民国政治学人却没有东北部士绅的笃定的现代国家基础,也没有职业政治学家所依赖的稳固的大学体制,乃至于在政治运动尤其是政权变更的影响下,便“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最终散入烟尘。反而是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治论述正合中国革命实践的主线。在非正规化的学校体制之下行政治训练之实,以政治学院/政治学校的组织建制,厉行干部训练的政治教育,最终形成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为核心、以社会主义为实践的政治知识体系。这套政治知识体系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政治课散布于国民大众,以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和民族解放运动研究为理论体系形成了一套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学概念体系。倘若说,1949—1978年间,其在苏联模式的背景下艰难探索,那么,1979年后欧美政治学的再次输入,使其在比较政治学视野下基本完成了转型期的政治知识论证,从革命党到统治党再到执政党的政党国家论述是其最大成果。回到主题上,中国政治学史的概念建构如何进行,如何让国际同行认同中国政治学史的社会科学化概念建构?大概有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需要厘清:第一,回到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解释历史。现实尤其是未来的想象与建构起始于对历史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应当从元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源问题出发,因为作为历史之具体形态,源流总是地方性、独特性的表现,而现实世界总是多源流并行。回到元问题和回到事实,就是回到“理一分殊”中的“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任何事物的产生总有其设定,回到最初的设定,就能看到它在历史地域上的独特呈现过程。第二,元问题在不同地域有其分流,并以地域性概念系统为表征。在美国现代政治学史上,有政治学系、知识生产、学位制度、发表制度、专业期刊、政治学会等关键概念;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史上,则有政治学院/政治学校、政治教育、政治传播与教学以及知识生产、发表制度两套概念系统。第三,在这两套概念系统中,都有其核心的分析性概念。如美国政治学中“美国”的分析性含义,它显示出是关于“美国”而不是“欧洲”更不是“中国”的政治知识论述,“理解美国”是美国政治学史理论递进的根本动力;中国政治学亦然,“中国”是其分析性概念,它是“理解中国”在政治知识领域的产物,它也随着“理解”上的更新而创造出更多的中国本土政治概念。第四,在历史或经验叙述中提升概念的“链条活性”。相较于知识与理论,历史与经验的事实属性更具有独立性,更易于获得研究者的承认。“我”不信任你的理解与解释,但是,“我”尊重你看到的事实,也希望能够看到你所没有看到的事实,因此,历史与经验的事实是概念建构的基石。而论证技巧的严谨、论证技术的完整,更容易获得读者的支持。第五,如何让国际社会科学同行认同中国政治学史的概念建构?一方面,仍然是回到事实,中国政治学史的历史事实与美国不同,回到事实能够打破既有的概念认知桎梏,进而重塑概念;另一方面,遵从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规则,用严谨而完整的论证实现概念的理论化。引用格式:王向民.回到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政治学史研究的概念建构[J].理论月刊,2024(10):7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