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姜宇辉教授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公众号发文《哈伦·法罗基在中国:三个展览,一种坠落》,公众号转载全文与读者共享。
《手的表达》 © Harun Farocki,1997
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在名作《屏幕上的受苦者》开篇曾将当今时代的状况和症候明确而又尖锐地界定为“无根基性(groundlessness)”。这个界定也足以令我们深思法罗基的影像实验的真正动机。是的,这个世界自去魅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全面趋势以来,一直都在丧失它的各种根基,从历史的根基(传统),思想的根基(本原,archē),直至大地这个最直观可见的基础。今天的我们,虽然还以岌岌可危的肉身“栖居(dwelling)”于大地之上,但那至多只是一个陪衬的背景,测量的基准,感觉的边界;而真正的“基础”,早已在一个元宇宙和生命3.0的时代日渐被整体性地移置于数字空间和数据海洋之中。
从某种并非含混的意义上来看,法罗基的创作也始终、最终在回应这个根本的命运乃至厄运。关于他的身份和创作的特征,向来已经有各种界定,比如论文电影,实验影像,具有强烈政治性的纪录片等等,但对于一位出色艺术家的研究和总结,不应仅停留于这些局部和细节,还更应该直面他所要回应的根本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在他的生命接近终点,创作接近终结之际才或明或暗的显露出来。是的,我们所指的正是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年所创作的惊世骇俗之作《Parallel I-IV》。表面上看,这部难以归类和综述的影像作品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围绕电子游戏展开探讨数字影像的历史演变,但在法罗基所擅长的比较和隐喻的手法之下,“无根基(groundless)”,“去根基(unground)”这些颇有哲学意味的主旨极为清晰地展现出来。在这部四乐章的影像交响诗之中,几乎每一章的结尾都会以“堕入虚空(enter the void)”作为最终的启示(Revelation)。最扣人心弦的当属其中的两个场景。其中一个先把目光和镜头铺展在数字生成的逼真而生动的水面之上,但随即就慢慢地潜入到水下,顿然间暴露出那个空空如也的巨大深渊。如果在法国巴黎的68运动之中,“街道之下是海滩”本是一种豪迈的行动宣言;那么,“数字表面之下是空无”,这个法罗基所苦心孤诣地营造的的顿悟式场景,更多表达的就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绝望乃至恐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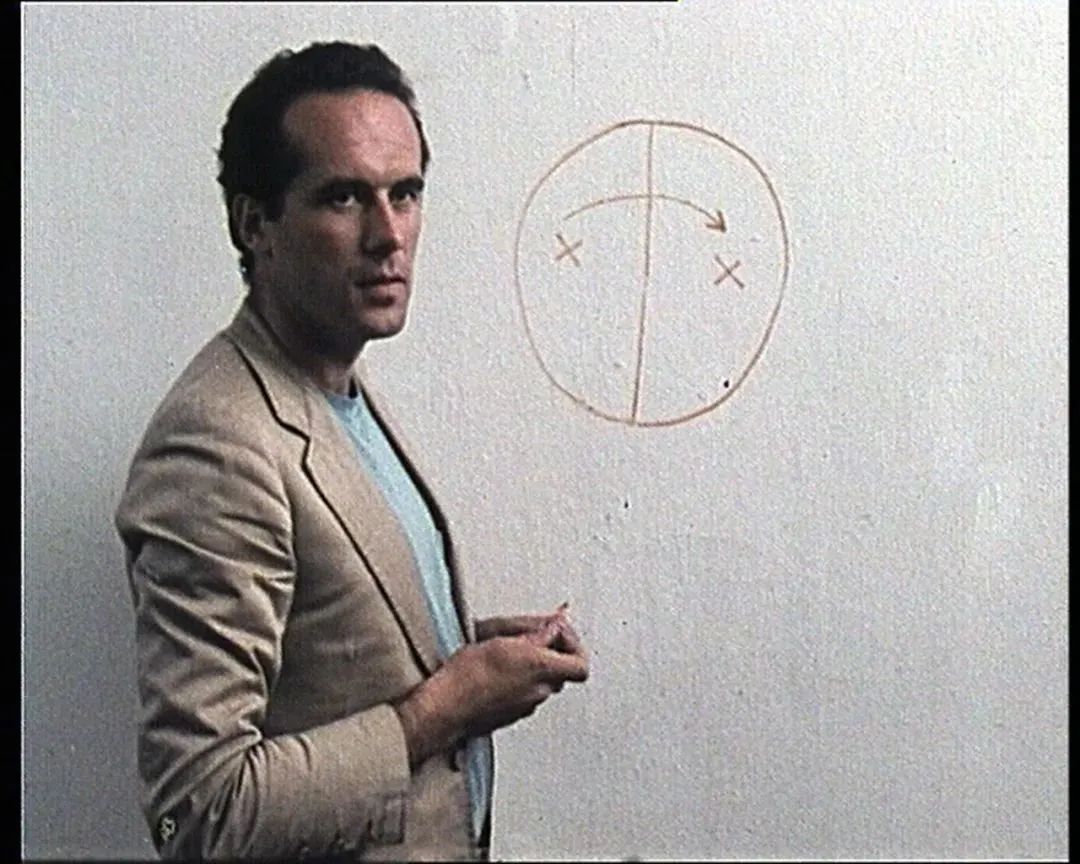
《叙事》 © Harun Farocki, Ingemo Engström 1975
但在另一个场景之中,此种恐惧惊悚的体验甚至慢慢凝聚为、升华为一种涅槃式的终极冷静。一片在电子游戏之中随处可见的数字风景,当我们慢慢地拉远镜头,直至无限远之时,它最终就会呈现为悬浮在无尽虚空之中的数字岛屿。而那甚至都不能说是悬浮或漂浮,因为我们都看不到任何作为基础和背景的介质,无论那是浩瀚的海洋,还是无垠的太空。不,那是终极的,完全的,彻底的空无。而所有今天我们置身其中的看似美轮美奂的数字景观,最终都搭建于、悬空于、甚至消失于这个吞噬一切的空无之中。在这里,作为观者和思者的我们似乎意识到了法罗基与史德耶尔的一个根本区分。面对整个世界的无根基性宿命,史德耶尔试图以更为极端而强力的“坠落”来进行对抗:“坠落是堕落也是解放,是一种将人变成物(反之亦然)的情状。”[1] 但法罗基则正相反,他即便也试图将世界抛入虚空的深渊,但他的那些影像实验却采取了一个相反的运动方向,即不断上升,不断拓展视角,进行俯瞰,尝试遍览。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史德耶尔是一个激烈的行动者,那么法罗基在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一个终极冷静的哲学家。
或许正是洞察到了这个核心要点,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在他概述和阐释法罗基的重要论文的最后就豪不隐晦地抛出了自己的质疑:“法罗基一次次地表明,他的意识从世界图像中抽离出来,但是,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他自己的操控可能就没有意义了。”[2] 但果真如此吗?法罗基在最后的作品之中,真的暴露出自己的那种“上帝视角”的隐藏动机了吗?还是说,他的哲学式的俯瞰与洞察本就有另外一种面貌与内涵,甚至可以被视作是远比史德耶尔更为极端而彻底的另一种“坠落”?
《如何生活在联邦德国》 © Harun Farocki, 1990
这个追问,恰好在法罗基与中国的关联之中得到了全新的启示与线索。中国,尤其是世纪之交的中国,也正呈现出极为鲜明而剧烈的去根基的运动。我们正在抽离自己的传统,同样,我们甚至正在全面地离开自己生兹在兹的实在空间。元宇宙这个概念在中国持续掀起的热潮,似乎也正彰显出我们对于那个沉浸的、拟真的、遍在的数字空间的向往乃至迷执(obsession)。而在这两极——斩断历史之“根”,远离实在之“基”——之间的,恰好是新冠这另一个具有深刻深远影响的事件。蔓延而强力的病毒,展现出的是另一种去根基的厄运,那正是对生命之根基的抽离与偏离。当我们的肉身生命之中密布着共生的病毒和抗体,渗透着各种人造药物和电子微件之时,我们自己似乎也正在全面丧失人类之根基,主动被动地迈向“后人类”之演化阶段。
而法罗基的作品自进入中国,直到今天,也亲历着、见证性这些根本性的去根基事件。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国的艺术家和大众的关注与厚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不仅是一件件舶来的艺术品,而且更是足以成为反观、洞察中国现实的一面面镜子。作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圈的观察者和参与者,我自己所能做的也就是结合三个重要的展览去展现其中的艺术手法和哲学内涵,进而尝试揭示法罗基与中国之间的种种“平行”关系。
2014年,哈伦·法罗基在中国 ©歌德学院(中国),摄影:张枝摞
法罗基与中国的渊源颇深,甚至多少有几分命运纠葛的意味。就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2014),在北京的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仍然策划有一系列以他为中心的展览活动。他将生命与创作的最后一站留给中国,是否也是一种命运的暗合?而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作品在当代艺术圈所引起的热潮并未止息,从2018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大展在北京,上海这些作为文化艺术中心的大城市举办。我们无意对所选取的这三次展览的细节进行重述,而只想基于三个根本的要点来展现其中贯穿的“坠落式反思”的主线。著名电影学家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曾将法罗基的创作宗旨概括为“令不可见变得可见”[3]。而虽然他未明言,但在那些林林总总的图像背后,始终有待被呈现和揭露的正是那个不可见的终极之空无。那么,法罗基用来实现此种“由空入实”的基本手法又有哪些呢?埃尔塞瑟总结出三种,即总体性视野,反思性态度和“隐藏的中心”[4]。这多少有些更接近电影研究的视角了,而我们在这里试图从更为广阔的影像创作和思想实验的角度,结合法罗基自己的诸多访谈和文献,将这三个视角进一步明确界定为真实的影像,物质性的突显,主体性的立场这三个要点。它们也反复交织、错综呈现于这些展览之中。
《让-马里·斯特劳布和丹妮拉·惠蕾在卡夫卡小说“美国”的电影拍摄过程中》 © Harun Farocki, 1983
第一个展览是2018年底至2019年的长达半年的、在北京缓存空间所进行的《哈伦·法罗基:图像搏击者》系列展览兼学术活动。仅从这个标题上来看,“搏击(wresting with)”显然同时强调突出了上述三个要点:它试图展现出图像的肉身与力量,进而在与图像的“角力”的过程之中进一步激发观者对自身的主体性反思,由此最终直面“何为真实?影像何以洞见真实?”这些根本的难题。但正如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独特的氛围与情境,每一次展览其实也有着不可还原、无法抽象的特殊背景。这次展览中的很多标题和阐述都已经鲜明提示了这一点。但我们在这里更为清楚地注意到“真实性”这个根本的关注。展览的第一个系列分三个主题(“政治散文与图像起义”,“操作图像与一体化(Verbund)”,“劳动实践与直接电影”)展开,展映了7部经典作品,从《不灭之火》开始,到《对比》收尾。这就触及了“影像与真实”的三个不同面向。首先,在第一个主题单元之中,影像显然展现出那种介入到现实的政治活动之中的积极力量。影像,不只是见证或纪录,也不仅限于暴露可见事件背后的那些不可见的错综复杂的力量及其格局,而更是能够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激发观者的共情,思考乃至行动。直面影像,单纯的“旁观”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以全身心地方式去卷入其中,飞蛾扑火,甚至死而后生。这正是法罗基进入中国的第一次震撼性的事件,它不仅改变了人们面对影像的常规方式,甚至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家对当代艺术的作品和展览的通常态度。尽管“介入”,“参与(participation)”每每成为展览文案和学术论文的关键词,但从《不灭之火》开始,中国的观者似乎才真正第一次感受到影像自身所直接传递的力量。那种不可抗拒,摧枯拉朽的力量。那种使人崩溃,但同时又令人重生的力量。展览的第二个主题单元进一步将影像之力量与更为广阔的经济生产与技术框架密切关联在一起,并最终引向了第三单元中的《离开工厂的工人》这部或许最为中国观众熟知和喜爱的作品。而关于劳动这个主题,仍然还是埃尔塞瑟给出了颇具洞见的解说:在法罗基的镜头之下、思考之中的人类劳动,也同时需要从可见向不可见进行视角转换。可见的劳动相关于各种明确的经济制度、生产关系,但不可见的劳动则理应在阿伦特的意义上将其界定为最为基本的“人之境况(human condition)”[5]。而在全面进入数字时代之后,当劳动也日渐彻底抽离了它的各种根基(从肉身存在到物质资料),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的生存形态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呢?从影像之力量到人类之命运,这似乎一开始就是法罗基在中国所引发的激烈思考与深刻触动。
《严肃游戏I》 © Harun Farocki, 2010
而于2019年下半年在上海的昊美术馆所进行的“严肃游戏”展览,又将对影像的思考进一步带向了一个更为当下也更为直接的阶段。如果说在《不灭之火》这样的作品之中,不可见的影像之力多少还只是在隐喻或体验的层次上起到激发心灵、唤醒自省的作用,那么,当世界全面进入到周蕾(Rey Chow)所谓的“世界标靶(World target)”的时代,影像自身的那种作为杀伤性武器、毁灭性暴力的狰狞面目正变得极为清晰可怖。大至全球定位系统,小至无人机和电子游戏,各种图像和影像早已不满足于再现、纪录甚至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常规的作用,而更是将自身的力量渗透、贯穿于上天入地、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严肃游戏”,这并不只是游戏产业的一个术语,它同样也是法罗基自身所酷爱的隐喻手法的一个鲜明体现。“一个人必须相信,并且让别人也相信:那些有待发现的东西,存在于微观层面上,存在于细微结构中!”[6] 法罗基的这句重要断语(assertion)正是对“严肃”这个隐喻的根本界定。严肃,绝非只是一种正襟危坐且往往带有明显权力背景和等级关系的立场,而其实更接近弗洛伊德所谓的“诡谲(Uncanny)”式的探问方式,即在看似平常熟稔的日常表象之下,去撕裂开那些陌异而刺痛的真实。清醒着,苦痛着,思考着,正是严肃之真意。而几位策展人在对谈和讲座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的“触感(haptic)”与“实地”这些要点,又极为敏锐地将法罗基与中国之关联带向了另外一个层次,不再仅仅是近乎宏大的叙事(“何为真实?”),较为抽象的思辨(“人的境况”),而更是以微观的方式探入到今天的那种被数字所渗透和操控的日常生活。反思影像之力量、忧思人类之命运,如今更应该落实于“触感”这样的人与影像交互的细节的、亲密的、肉身性的环节之中。严肃对待影像,这首先要求我们严肃对待自己的生活。在那看上去如此波澜不惊甚至平淡无味的表面之下,我们的生活正堕入到那无尽的无根基的深渊之中。这正是中国的艺术界对法罗基式的“坠落”的另一种解释。它当然不同于福斯特所质疑的那种置身事外、超然物外的上帝视角,而更接近与数字影像之“肉(flesh)”的交错(Chiasme)与纠缠(Intermingle)(借用梅洛-庞蒂晚期的这些术语)。同样,此种“坠入物质”的运动也与史德耶尔式的激烈而充满强力的坠落运动有着鲜明差异,它固然也不乏某种强力,但却更如幽微的触感一般,在玩家的每一次操作和触键之间唤醒着苦痛的创伤,自省的体验。
而这种在2019年间尚且隐藏着的主体性创伤,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刺激与冲击之后,再度集中爆发于2022年在昊美术馆举办的“皮肤之下,机器之间”之中。法罗基在其中虽然只是一个参展的艺术家,但“皮肤”这个触感的隐喻,“之下”、“之间”这些典型的手法,都极为鲜明强烈地呈现出别样的法罗基式的“严肃”氛围。而同样举办于2022年的展览“新生还者(New Survivors)”之中,策展人王姝曼不仅将创伤上升为一个形而上学的主题,更是再度回归了《不灭之火》这部经典,在致敬大师的同时,也给所有中国的观众带来一种时空轮回的宿命感。法罗基式的火焰,尽管偶有蛰伏,但从未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历程之中熄灭。从宏大的哲学命题,到微小的生活细节,再到深切的创伤体验,它的每一种炽燃,都在呼应着中国社会变革的脉搏与呼吸。而我们,也同样需要一次次回应着他的呐喊,去坠入世界的深度,堕入数字的空无,重新思考“人是什么”这个终极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