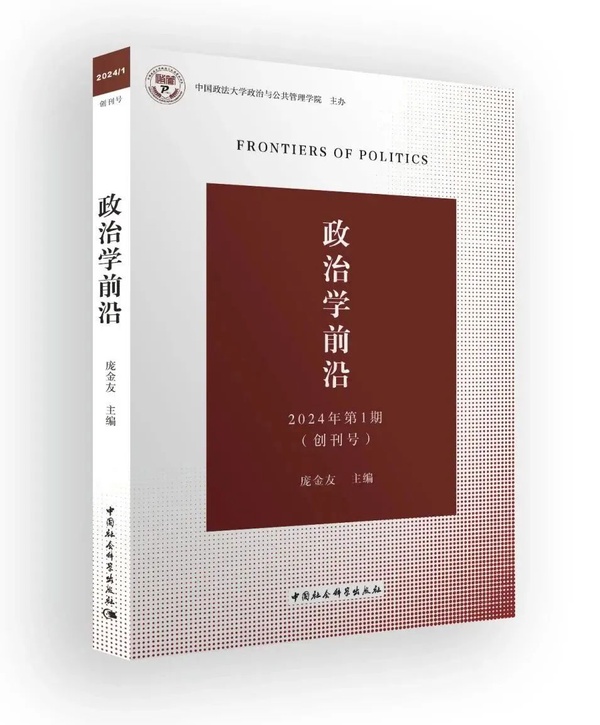编者按
2023年8月25日,政治学人平台“编辑有话说”第二期活动邀请《政治思想史》杂志主编、天津师范大学刘训练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与北京大学段德敏长聘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周保巍副教授等共同研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 现状与展望”。《政治学前沿》2024年第1期(创刊号)笔谈栏目即根据三位老师的发言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内容详情
01
首先非常感谢 “政治学人” 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分享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另外也特别感谢前面两位老师的分享,自己也非常受教。我的发言题目是“建立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血肉联系”。前面段德敏老师的发言题目是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思考”,其实我今天的题目也是讲 “之间” 的。段老师讲的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我今天要讲的是在思想与现实之间。如果段老师刚才的发言题目让人想到阿伦特以及阿伦特的一本名著《过去与未来之间》,那我希望我今天的发言题目也会让大家联想到政治思想史上另外一位牛人和另外一本名著,那就是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先生的一本名著——《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如果大家读过这本书,其实也可以把这本书叫做 “在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之间”,也就是说这本书实际上也是讲 “之间” 的。它的意涵是什么呢? 它的意涵就是说: 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在思想与行动之间展开,也就是要在我所说的思想和现实之间展开,要在思想和现实的关联和互动中展开。或者推而广之,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要在理论和实践的关联和互动中展开,在词与物的关联和互动当中展开,在观念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中展开,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当中展开。
首先,我要做一个简单地界定。这里面讲的思想 (对我们的思想史研究者而言,可能也不需要解释) 包括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也即理论、哲学、意见、原则、价值、理念,也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头脑中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甚至有一些是虚无缥缈、不可测度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观念世界。那么与我们的观念相对应的、与我们的思想相对应的现实又是指什么呢? 我认为它可能包含有两个层面的意涵。第一个层面是指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思想所由以诞生的那个现实世界。比如说我们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性思想所诞生的十五、十六世纪意大利和佛罗伦萨的现实处境和现实状况;还比如霍布斯的绝对主义思想所诞生的17世纪英格兰的现实处境和现实状况。现实的第二层意涵,我认为是指我们作为研究者所置身的那个特定现实处境和现实境遇。比如说刘老师,包括段老师都研究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也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而是生活在现实的处境、现实的困惑、现实的问题当中,他们研究马基雅维利,也一定是从他们所置身的现实处境和现实视域出发。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层面的现实统称为生活世界,一个是指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一个是指我们自己作为研究者所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
下面我要说一下我的主要结论,其实也不是我的结论,而是被一些一流的政治思想研究者所一再证实了的一个观点,或者说被一流的政治思想家所达成共识的一个观点: 一切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它必然会致力于重建思想和现实之间的血肉联系,必然会致力于疏通思想和现实之间的血肉联系;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必然会定位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一个交叉和互动地带。就像年轻一代新锐的思想史学者,剑桥学派第三代传人、哈佛大学教授纳尔逊(Eric Nelson) 所指出的: 任何政治思想史的作品都必须从一系列关于观念如何与现实生活当中的重大转折性事件之间进行互动这样一个假设开始。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借助于希腊的一个神话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这个希腊神话故事讲到,地母盖娅之子安泰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大力神,但他一旦脱离了大地,就会丧失所有的力量。同样,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旦脱离了政治思想在其中诞生、孕育、发挥作用、产生后果的现实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母体,一旦脱离了研究者自身的现实处境、现实关切,以及由它们所激发和产生出来的同情共鸣,缺少了这种由现实感所产生的切肤感或者切己感,就会丧失所有的力量,就会丧失我们政治思想研究所应该具有的想象力、洞察力、解释力和生命力,就会变成一堆陈芝麻烂谷子的无聊且无意义的陈年旧事。政治思想史就会落入到以赛亚·伯林所描述的那种可怕状况中: 伯林说,一些政治思想史研究做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笛卡尔这样说,斯宾诺莎那样说,休谟认为他们俩说的都不对,这都是些死气沉沉的东西。” “除非你对所讨论的思想深感兴趣 (注: 我们知道,思想史研究者对什么感兴趣,一定跟自身的现实处境有关),否则不论你自己看法如何,思想史就总是与你无关的、死板的、索然无味的东西”。
02
这就是说,任何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回到思想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双向互动的和相互塑造的关系当中。既要考察现实和生活世界对我们思想和观念世界的塑造,也要考察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世界对现实和生活世界的建构,不断保持着从现实到思想、从思想到现实的无尽的往复循环,保持着两者之间的血肉联系。这就意味着政治思想史本身不是在一个封闭的内循环当中来处理思想、观念,而是在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制度史的关联和互动中来考察和处理思想、观念。其实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意识到,政治思想史当中的一些问题及其答案,往往不是从政治思想史本身当中来寻找,而是要在政治思想史之外来寻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功夫在诗外” 的言外之意。
我们可以以现代早期的人性论为例。很多现代早期的思想家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激情而不是理性,而在激情当中又更加强调的是 vain-glory,honor、pride、self-liking 这样的一些东西。尤其我们会注意到现代早期的很多思想家在讨论人性时,一直在探讨人的自我评价(self-estimation)问题,讨论我们为什么会高估自己,为什么会低估自己,讨论人的身份、人的尊严问题。不仅霍布斯在《利维坦》当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这些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讨论这样的问题? 如果仅仅细读他们的文本,我们确实能够知道他们关于人性论的观念是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去建构这些人性论观点的。但是如果我们要问: 他们为什么会秉持这种人性论而不是那种人性论观点? 又或者他们为什么以这样一种方式,而不是以那样的一种方式来建构自己的人性论观点? 我们不能仅仅通过阅读文本,通过探讨文本内部的逻辑关系来得出答案。实际上,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要进入到政治思想史的外部,从长时段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中去寻找可能的答案。
如果我们回顾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兴衰沉浮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20世纪的后半叶,政治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能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地窖上升到阁楼,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思想史研究重新恢复并重建了思想和现实之间的血肉联系。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在斯金纳他们崛起之前,按照伯林的说法,政治思想史研究是非常寂寞、非常孤独的学科。就像斯金纳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思想史研究里的另外一个学派——苏塞克斯学派(Sussex School)的一位重要的成员温奇(Donald Winch)所说: 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史家,每次外出去作讲演、作报告,都好像是在进行一场客场比赛。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都会面对心存狐疑,甚至心存敌意的听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著名的宪政史家纳米尔爵士(Sir Lewis Namier),他对政治思想史的敌意是非常明显的,不加任何掩饰。他在与伯林交谈的过程中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在所有的历史学家当中,观念史家其实是最没有用的”。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这当然和当时占主流的实证主义和实在主义的哲学传统有关。我们知道在实在主义或实证主义的传统里面,他们认为观念、思想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难以测度的,所以在证据等级上都处于比较低的等级。除了跟我们讲的实证主义传统有关外,政治思想史的低迷和边缘其实也跟我们传统的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的做法有关。就像写出了著名的《革命政治与洛克的<政府论>》这部经典名著但却英年早逝的阿什拉克夫特(Richard Ascraft)所说,在传统的观念史里面,观念成为脱离了现实的、悬浮在空中的、浮游无根的东西,就像 “一直在平流层当中自由漂浮的过眼烟云”。在他们的研究当中,思想与现实、观念与行动完全是割裂的,就像是两个没有任何交集的平行世界。
这里面也有一个关于伯林的故事: 伯林之所以抛弃纯粹概念的、演绎性的、逻辑性的分析哲学而转向思想史,是因为在1944年从美国坐飞机到英国,跨越大西洋上空的时候,他突然顿悟到纯粹概念性的、逻辑性的分析哲学就如天上的浮云,它与现实有何干? 它与我们天下苍生又有何干? 这其实是在20世纪上半叶对思想史的敌意和不满的一个普遍源头。执掌剑桥大学的钦定皇家现代史教席的埃尔顿(Jrffrey Elton)在演讲时就曾讲到,“思想史根本不算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思想史很容易失去与现实的联系,而且实际上思想史是远离我们真实的生活的”。但是,如果我们研究政治思想史就会发现,就历史的实际状况和实际进程而言,事实并非如此。即便在我们现在看来,最为抽象的那些概念,最为远离现实生活的那些形而上的概念,比如现代早期我们认为是虚构的 “自然状态” 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它在当时都包含着最为真实的、活生生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比如现代早期的宗教内战和政治内战的经验,比如当时四分五裂的封建无政府状态这样一种生命体验,就像丸山真男所讲的: “欧洲的政治学概论看上去描述得很抽象,实则其背后蕴含有欧洲数百年来的政治历史脉络,哪怕只是其中某个命题,也是在其现实的变化波动中孕育而成的。所以不管针对哪个范畴或者就某个命题进行解析时,最终都会体现到欧洲活生生的政治现实中去。” 即便是像康德这样穿着最为强固的理论紧身衣和重重概念盔甲的思想家,貌似最超脱于现实生活的思想家,实际上也是如此。比如在海涅的笔下,康德的每一本书都包含有具体的现实考量和目的。在海涅看来,《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含有最为明确的政治宗旨——那就是要砍掉自然神论的头颅。
所以,我们政治思想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复活凝结在各式各样的抽象概念和形而上学术语当中的那些已经逝去的、但曾经非常鲜活的生命体验,以及它们的现实质感,重建他们当时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图,重建它们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这也是我们通过考察20世纪后半叶思想史 (包括政治思想史) 的复兴过程所得出的一个基本教诲: 那就是思想史研究不能够一直悬浮在半空中,要下降,要落地,要回到其母胎和力量之源,也就是要回到虽然粗糙但却坚实的地表,要扎根于大地,要扎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要回到我们研究对象的生活场景和现实处境,回到他们的所知所感、所思所想,回到他们的困惑,回到他们所面临的最为棘手、最为紧迫的问题。不然,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就会一直悬浮于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现实关怀之上,变成观念世界内部的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一种文字游戏。从观念到观念,从概念到概念,这样的话,我们只能从事于观念内部的逻辑建构,或者是从事于观念内部的各种概念的分殊、梳理和辨析。这样的一种研究,即便是穿着最精致的学术外衣,包裹着最高大上的学术行话,它们也都只能就文本谈文本,就观念谈观念,在文本内部谈文本,在观念内部谈观念。好像文本所构成的观念世界是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是一个严格的、封闭的、密不透风的、自循环或者内循环的系统,好像这样一个封闭的系统内部的思想和观念可以在不依赖或者不借助于任何外部因素,在没有任何现实刺激的情况下,就可以无限地自我繁殖,无限地自我增殖。
03
针对这样一种割裂了与现实生活关系的思想研究或者文化研究,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reetz)就曾经对之进行过辛辣而犀利的讽刺。他讲了一个关于印度人的故事。他说有人问印度人,“世界为什么能够悬浮在空中呢?” 印度人回答道,“被一只大象驮着”;“那大象又是被什么驮着呢?” 印度人回答道,“被一只乌龟驮着”;“那乌龟又被什么驮着呢?” “被另外一只乌龟驮着呗”。
这是一个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又能从这个寓言故事中获得什么样的教益呢? 在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当中,在我们寻找问题的最终答案以及因果关联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沦入到印度人的这种窘境: 从大象到乌龟,再到另外一只乌龟这样一种无穷无尽的封闭循环。同样,在我们的思想史研究中,我们也要避免沦入到从观念到观念,再到另外一个观念,从而形成一个 “完美” 的闭环和内循环,由此丧失了将我们所研究的观念世界与我们所置身于其上的、坚硬的、坚实的地表关联起来的机会,由此丧失了将我们的观念世界与我们在其中生活、思考、行动的政治经济现实联系起来并加以研究的机会,从而也丧失了将我们的思想史研究从封闭的内循环升级为一个开放的外循环的机会。
最后,我想就我们现实中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谈一点看法。我们当下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就像前面几位老师所说,近年来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包括就像刚才训练老师所展示的精微的概念辨析,包括致力于重构观念、文本内部的逻辑关系,甚至开始重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思想家与思想家之间的辩难。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现象,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但这远远不够。我认为我们可能更加欠缺的、可能更加需要重构的是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对话,是观念和行动之间的对话。这也是我在这里一再强调和呼吁的要重建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是我的一点粗浅看法,希望能得到各位老师、各位同行的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注释从略)